牛贩子山道雁宁
布谷鸟叫得朦朦胧胧不知它在天上地下还是山林旮旯里,太阳也把自个儿闷在银白的云团中好半天不肯露点脸角,可那黄澄澄的春光依然漫沟漫坡地泼洒,凡是带绿的东西都生光发亮,连那棕褐色的山岩也长了精神。 浩成打量脚下这条歪歪斜斜朝前爬行的牛贩子山道,它有多少年辰谁也讲不清楚,有多少牛贩子和黄牛水牛从上面走过更没人讲得清楚,那坚硬厚实的豆青条石已被足板牛蹄踏得坑坑凹凹,显得老态龙钟疲惫不堪。青条石之间的缝隙里缀着蓄满水分和阳光的小草,晶晶莹莹,欢欢实实,稍一静心就听得见它们嗞嗞生长的快乐呻吟。他是个二十出头的青年汉子,身架子不小却长得秀条一点,脸庞也白净了一点,唯独那对眼珠子乌乌黑黑明明亮亮,说多机灵就有多机灵。一副牛贩子相!这是人家骂他的话也是他最恼恨的话。他憋了气就走到后坡,朝那一片青乎乎的坟地喊——爹啊,你当了一辈子牛贩子还要你儿子脱不了壳壳么?!他曾赌咒发誓,断手断脚也不走这条鬼气森森的山道,娘一听说它,脸就堆了乌云暴雨,好像一个闪电就会湮灭心湮灭眼,血流似涨桃花水一样嚯嚯叫嚷。可他还是来了,恨恨怨怨地走在这古而又古、老而又老的牛贩子山道上。 他身后跟着两头牛,一头又高又大的水牯子,四膀漩儿磉磴蹄圆,两只板角乌黑发亮浑身皮毛油光水亮,真应了牛市里形容好牛的口诀:前能放张斗,后能夹死狗。板栗坡上那几冲硬实实的苕板田每年翻春都要犁趴牛,春儿爹回回都守着口冒白沫的牛朝山岩那边嘀咕:牛板筋吔,你吃牛饭穿牛衣就没给老哥牵回一条能降服板栗坡的牛,反而摔下老岩叫我赔了几泡子眼泪水水。承包田地那阵,春儿爹横跳竖闹不要那几冲田。他想着爹的死,恨着一口气包下来,用一柄尺长大锄也狠劲弄了几年好收成。呸呸!你硬!你硬!看看老子硬还是你硬!呸呸!他总是这样咒骂着,快快活活地挖田。到前年村里发生变化,狗娃一伙砖瓦匠到陕西河南去承包高房大屋,美其名曰劳动力输出!蛮牛一伙打石匠开了大理石场子,美其名曰开发本地资源!都来求他,浩成浩成田土给你种,随便匀点粮食给我们家里就行。毛根儿朋友不应也得应,再说也不能让那么多那么好的田土荒芜。农民头一回不在乎田地。浩成几乎成了地主。苦干一年收成倒是好收成,可把一条瘦牛累成了牛肉汤。他想起了牛贩子山道,咬咬牙背着粮,来了。 水牯子后头是条短角板粗颈项厚背脊皮毛像黄缎子一样绒软放光的黄牯子,一灰一黄好神气。春儿说,浩成哥买水牛也要买黄牛,犁坡坡上那些小水田黄牛比水牛还行哩。她的声音总像唱山歌甜甜柔柔,清清朗朗,他一听脑袋胸口都热烘烘恍惚惚的,真想在她红润润的腮帮子上摸一把,黑油油的长辫子上捏一把,可他伸不出手,伸出去也许就收不回来,开朗得有点儿野气的春儿那对水雾雾的眸子正巴望他把她抱进青㭎林哩。 喂,小老弟,你发啥神经嘛,赶路就赶路,你那黄牯子不在松树桠换副掌子,腿杆谨防像我一样哦。离浩成十几米远,走着一个瘦精精,蓄山羊胡子,一对小眼珠贼亮的瘸腿老头,一张脏兮兮的黑头帕,在他剃得溜光的鸡蛋脑壳上缠得很不成章法,那破旧蓝布长衫腰头古怪地结了一圈草绳,手上的竹烟竿倒很漂亮,翡翠烟嘴黄铜烟锅,一根金竹足有五尺长。他背后跟着一条雄健异常的黄牛,懂行的人一看见它就会喜欢得忘了老婆,乐滋滋地骂,狗日的硬是牛魔王的种,一匹山都拽得动哇!它粗脖颈上吊着一条红布巾子系住的铜铃铛,一路破响破响,又壮威风又煞风景。 瘸腿老头是个老牛贩子,他一进牛市,所有卖牛的、买牛的都拿眼睛挖他,凡他拍过角板的牛马上都涨价。他转一大圈就蹲在这条黄牛的腿边抽烟,听卖主买主讨价还价,等几潮人涌过了,才猛不丁儿站起身,用眼斜刺着卖主有气无力说,妈的上当就上这一回,牛老子要了,就按你哥子开的价!卖主一愣,明知吃亏也不好改口,赔着笑脸和他去开票付钱。浩成早看上了这条牛,心头开的价比瘸腿老汉高许多,可也只有眼巴巴看着他用鸡爪般干枯的手把那个破铜铃铛系在牛颈子上。难怪他外号叫牛板筋的爹,总抱个酒罐罐,挂一张红脸哼哼道:牛市像个海,要好深有好深,日他娘虾米鱼龙啥角色都有呢。也许爹来也会输在他手头,你看那眼珠子好盯人,多被他看几眼面皮都会脱一层。管他的,我又不是牛贩子,到龙头岩牛市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可浩成好奇怪,自己对水牛黄牛都像有天生的识别能力,是好是坏是贵是贱一看就准,在那个大巴山区最大的牛市里简直如鱼得水自由自在,真他妈牛贩子的种!若不是他爹就死在这条山道上,他真会再去二次三次,也定会搓磨成比那鬼老头还鬼的老牛贩子。 破响破响的铃铛声又叮叮咣咣给山道添了几分苍凉。天是一条狭长的白带子,夹峙山道的山岩又高又陡,棕褐色间仅有些斑斑驳驳的绿意。巨大的鹞鹰在岩壁间窄小的空间盘旋,卷起一股股风刮得碎石叫唤着直滚,它忽地翅膀一抖不抖斜插下来,一副能叼走牛的气势吓出人一身冷汗。 路不难走石板却费脚力,浩成的灰灰和黄黄腿劲有些软乏,跨步的姿势笨拙多了。他这才明白,为啥龙头岩牛市的牛价要比竹溪镇便宜得多。 天上起云云重云依哟, 妹儿身上裙重裙吔嘿, …… 瘸腿老汉悠悠闲闲哼着野里野气的山歌。一出牛市他就跟上了浩成,嘴里说,小老弟同行一程前头就分手啰,走这半天反跟得紧,好像他们是结伙成伴的一老一少。山谷里除了这条山道绝无它路可走,老头子嘴上讲鬼话心头想的啥捉摸不透,偶尔回头,那双小眼森森可怕,笑起来也叫人起鸡皮疙瘩。他不由抓紧腰间那个家伙,心口溢出一股豪勇之气。一柄青铜短剑,他爹的遗物,据说是先辈人从数十丈高的悬棺里取出的,大概是以宕渠为基地的古代巴人的一支号称射白虎之裔的賨人的器物。爹常把它带在身上,有空就拿出来把玩,数千年的东西居然青光闪闪。他从不许娘动它,睡觉也压在枕头下,把骨肉摔得血糊糊的,它竟在他腰下完好无损没沾一丁点儿血渍。 瘸腿老头跟青铜短剑一样神秘,影子似地贴着浩成,他停他停,他走他走,像个青光闪闪的梦塌在他胸口上,把条深山野谷变得漫长无际,叮叮咣咣的破铃铛声摔得遍坡遍岩都是。那响声是一片白色。布谷鸟的啼叫也是一片白色。 太阳被白云一层一层紧紧包裹。岩壁上映出它挣扎的神色,那光有点苍老。比阳光更苍老的山道。被山岩一层一层紧紧包裹,成了皱纹重重叠叠的精怪。年轻的是野草灌木和在岩头试飞的幼鹰,还有浩成和灰灰黄黄的牛们,衰老的山谷生机充盈。 松树桠到了。奇怪的是岩上岩下全不见松树的影儿,倒有一棵老槐铺着绿莹莹的新叶绽出冷冰冷冰的白花,一股郁闷带着春天娇气的花香反使心子发沉发乱。槐树对面一排明目爽气的青砖瓦房,原先属于城里人的玻璃窗子也属于了山里人。铁匠棚子钉掌桩子一溜横在垭口,像道关隘要塞,老远就令人肃然起敬。 屋前坐着一位扎鞋底的女人,她腰粗脸孔却秀秀气气,分不出到底四十五还是三十五岁。她听见破响破响的铃铛声心头一慌针刺了手,赶紧把手指含在嘴里含含糊糊喊道:牛牛生意来啰,牛牛你就晓得听你那破收音机子,天下事懂完了也还要干自家的事,砖瓦房子还是你爹你娘一锤一锤打出来的哩。 又啰嗦又啰嗦,自从那个人摔岩死了,你就啰啰嗦嗦好烦人!牛牛是个膀粗腰壮黑黑的虎头虎脑的年轻汉子,脸和手臂呈红铜色,一对眼睛铃子般鼓着,颈间挂着全张羊皮且当抵挡那些灼人铁屑的围腰。他这长相架式简直像随同武王伐纣的賨人勇士。 当娘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瞪着儿子嚷:那个人咋个啦?他是你亲爹你是他骨血,你爹那个脓包就晓得到竹溪镇卖他的破锄头烂镰刀,待人像块冷铁砣子,你拿心拿血都暖不过来。我就是喜欢那个人,不怕丢人不怕现眼把你娃娃生下来。哼,他要敢讨我,屁股一拍我就跟他走,兴许他还能保一条命哟,我的冤家…… 牛贩子来了,你少讲几句留点口水养牙齿。清明节我去给亲爹上坟,该合你心意了吧,可你又不讲亲爹姓甚名谁家住哪里,当儿子的就那么心硬嗦? 牛牛一副好手艺,三下两下就把浩成那条水牯子套在木框子里了。瘸腿老汉一屁股坐在槐树脚下吧嗒吧嗒埋头抽烟,不时用眼角瞄瞄壮汉子牛牛和他的娘。浓浓白烟遮了他核桃壳般的老脸,连黑布头帕里也冒出丝丝缕缕烟来,他那有灵性的黄牯子却往桩子边走,像很明白要换掌,把个破铃铛摇得稀里哗啦不成个调。 喝茶喝茶解解口渴,老师傅小师傅换了掌歇口气再走嘛。今晚你们还是宿野猪峡的岩洞么?啧啧牛贩子挣几个钱也辛苦哦。别个不晓得我晓得……娘!牛牛一铁锤敲在铁墩子上。她闭了口把一瓦罐老荫茶放在瘸腿老汉跟前,衣袖一卷就帮儿子给牛换掌。她也是干这行的老手。 浩成插不上手就跳起身捋下一把槐花,掐出花蕊往嘴里丢舌头得到甜味就吐出来。浩成哥浩成哥帮我摘槐花花,我娘做蒸莱我把给你吃,好香哦好香哦。他坐在槐树枝丫上,春儿在树下蹦蹦跳跳,叫声笑声像喜鹊子一样清亮。二十多年前的一天,瘸腿老汉也这样蹲在槐树下抽烟。对面那间房子,不是瓦屋,而是破旧的茅草棚,一对结实精壮的男女,在里面撒野火……他本来很喜欢这个脸蛋红红、眼珠子像炭火样燎人的小媳妇,可年岁到底大她二十几,便耷下眼皮,任同行的年轻伙伴用几句山歌就轻轻巧巧把她勾上了手。这口气一吞就是几十年,茅草棚里的往事搅挠了他几十年,又飘忽而来,他忘了吸烟忘了埋头,痴呆地望着妇人的背,两颗黄浊浊硬梆梆的老泪悄悄爬在眼眶边欲坠不坠。 啊呀!牛牛娘眼花一闪,把那个在牛颈子上摇晃不定的破铃铛抓在手里,眼像两柄刀子刺在浩成脸上。小师傅这铃铛是你的么?他晃晃头,眼角朝槐树下一瞥。 牛牛娘顿时忘了一切,风一样奔过去。哎呀呀这不是拐子老哥么?二十几年不碰面,你你你——老啰。你老哥也真狠心,妹子得罪了你,我家门前的路没得罪你嘛,自从出了那回事,你连脚步也不朝这边跨。我这苦命也只有老哥看得仔细,守着这无土无田的寡岩过日子,难哦……泪珠儿成串地在她脸上滚。 是的,山垭口除了冷硬的岩石和几棵老树,看不见土更没有田,屋后那块菜地也小得可怜。这对一个农家女人实是一种折磨。浩成有点理解她对那个异乡汉子的私情了。 瘸腿老头拄着烟杆站起来冲她古怪地一笑,伸出干焦焦的巴掌拍拍她圆浑浑的肩膀。大妹子呃,不是老哥不想来,这腿杆不争气哟,提起像砣铁,拖起像条棍,羞人哦。那天他神恍神惚走到野猪峡就摔了岩,若不是他那尝足了女人滋味的年轻伙伴,恐怕命都丢了。牛贩子的日子风里雨里有苦有乐,要碰上个热心热肠真情实意的女人实在不易。他的好日子就这样一下摔落山岩被山风卷个干净。松树垭还能再来么?人世间有许多东西说得,许多东西说不得,憋在心里让它们慢慢淡慢慢冷。 牛牛娘忽地来了精神,端来桌椅捧出瓦酒罐,把一大块红亮的熟腊肉丢在老汉手上。老哥,今年不像往年,屋里头要肉有肉要酒有酒,要是牛牛的亲爹…… 当!牛牛的铁锤又在铁墩上重重响了一下。 她白一眼儿子,脸倏地绯红。 瘸腿老汉佯装耳背,心里却在嘀咕,我那老弟命好运好,得了这么个情痴痴的女人,为她摔岩——值得!牛牛的架子面目有点像他牛贩子爹。他从没后悔那次带了牛牛的亲爹同路,那个地道的大巴山血性汉子,他一结识就很看重。桃花天走桃花运才结好桃子。他把牛牛的脸看成一张红布了。 来来来,小师傅陪拐子老哥喝一杯,婶子晓得你们今晚里要宿老岩洞,不然明天傍黑赶不拢竹溪镇。小师傅你怕是头一回干牛贩子营生……牛牛娘猛地住口,两只黑多白少的亮眼珠死死盯住浩成腰间那柄青铜短剑,面色比槐花还惨白,一口气憋在她喉头不上不下咕咕直响。 浩成心想这女人是怎么了。只有春儿这么死死地看过他,脸也这么煞白煞白。那天太阳好大,春儿只穿件薄薄尼龙衫,胀鼓鼓的胸脯儿像要蹦出来,他忍不住伸出手去捏了一把,有说有笑的春儿立即就像牛牛娘这副模样了。不过,一会儿春儿双臂像藤子一般缠住他,两人像干柴一样倒在青桐林子绿茸茸的草堆里,惊得一对斑鸠咕噜噜往树丛里钻,逗得春儿格格地笑,桃花瓣似的红晕在她可爱的脸上放肆…… 牛牛娘瞪着青铜短剑发愣的一瞬,瘸腿老汉敏捷地跳一大步,把她遮住并推在椅子上。牛牛娘,要喝你就陪我喝,老哥这回上了松树垭也许莫得二回啰。各有各的生活,我妹子说啥也比你老哥强,该你得的得足了也该知足啰,不该得的看看想想也就算啰,来来来,喝喝喝。她吐出一口长气像把周身力气都吐尽了,软在椅上好半天也不动弹。瘸腿老汉抱起瓦酒罐仰面大灌,干瘦的颈子抽抽搐搐发出叽叽咕咕的响声! 牛牛娘的脸渐渐红润,心也渐渐平和,她轻呷一口酒算对瘸腿老汉尽了礼数。那张脸叫浩成想起春儿,他要赶回板栗坡好好看一看她,那熟悉得很的粉嘟嘟的脸,此刻竟模糊不清了。 牛掌换好啦,给钱。牛牛把铁锤往地上一丢,双手叉腰看也不看他们一眼。瘸腿老头伸手朝胸襟里摸,却被牛牛娘一把按住,她红光满面朗声叫道——不给不给,三条牛通通不给啦! 牛牛困惑地看着他娘,浩成也茫然不解,唯独老人心安理得地淡淡一笑,朝牛牛母子拱拱手,牵起牛就扬长而去。 走出老远浩成还感觉到什么东西在灼背,他不敢回头看那个木桩子似地立在老槐树下的女人。 瘸腿老汉变得异常沉郁,似乎一下子老了许多。 山道却在荒谷里蹦蹦跳跳,活泼得烦人。 灰白灰白镶了条条绿纹的山道弯来绕去像绞麻花,两边石岩突兀峭挺倾斜着像要合抱,天空被岩锋割裂成方型矩型条型棱型组合的一条亮晃晃的银带子,那根银带子飘到山谷底部已变得灰蒙蒙阴淡淡的。春儿说,浩成哥浩成哥,牛贩子山道上有个野猪峡,好险好险哦,我不让你去,今秋卖了粮食在竹溪镇买两条牛吧浩成哥。娘更是一听“野猪峡”三个字就脸青面黑浑身打颤,爹的尸身抬回来那天,她咒天咒地咒野猪峡,哭昏死过去。要不是县城开专业户会议,浩成还找不到离家七八天的机会,娘的眼睛像生了钩钩,他就上坡久一点,那又热又急的喊声就追来了——浩成呃——浩成呃——他却走入了野猪峡。 破响破响的铃铛声把死寂的峡谷闹动了,岩坡岩缝岩头的灌木丛里,扑啦啦飞出斑鸠呀、锦鸡呀、青背褡呀、铁嘴鸦雀呀,它们等候这热闹时刻早已迫不及待。哞——哞——牛们也兴奋异常,在越来越不平顺的石道上撒开了步子。 叮叮咣咣叮叮咣咣叮叮叮叮咣咣咣咣。 栀子花儿吔嘿嫩呀如油哟, 摘来那个揣在嘛怀里头, 叫声那个情哥儿依哟慢着些呀, 花儿那个嫩了呀不经哟吙揉呀…… 瘸腿老汉又撒开沙哑的喉咙,吼开野里野气的山歌。他唱得偏偏倒倒,像醉入了歌里,脸也像块老铜透出点光泽。往年子这个峡谷好闹热,兄弟们牛儿们一进峡口就吼开了——叽里哇啦哞哞哞哞——把趴在岩顶的石头野猪也逗得轰哇轰哇乱叫。牛牛娘的相好是只唱山歌的好雀儿,胸脯子是面牛皮鼓你一碰就响—— 黄豆林那呀哈小呀小豆叶哟, 贪花那个哥儿舍好哟好跑得, 半夜子时呀哈路呀路上走哟, 鸡鸣那个丑时舍要哟要离别。 哟喂情妹儿吔, 牛贩子哥儿命好孬哎嗨哟 妈的现时世道不古,这么好听这么舒气的歌儿都不大唱了,那些在电匣子里的哥儿姐儿,唱得依依呀呀酸不里叽老子才不爱听哩!唉,起先该求牛牛娘哼个山歌嘛,她的嗓子好水润好清甜好提神,就隔十面八面坡也听得清爽啊。这辈子恐怕再上不了松树垭啰,再听不成她唱山歌子啰,也罢也罢,那两只一公一母的唱歌雀儿,还在我胸膛里上下飞哩,牛牛都成壮汉子啰。 瘸腿老汉和他的黄牯子慢腾腾地走,被压在他们屁股后头的浩成和他的牛们,只好耐着性子挪腿杆,老人吼那山歌的野调野味,在心里搅起一股莫名其妙的骚动。 年轻人,你看你看,那岩壁壁上在演古戏哩,哎呀呀,好久不见还是那副样儿,叫人心子悬吊吊的。一面光秃秃不长苔藓没有水渍的赭色石壁,在灰白灰白的峡谷里似一团火,把四周的树木花草也映得霞红霞红,十几个大大小小方方正正人工斧凿的石洞,嵌在岩壁中段,有几个洞口还露出风朽的棺木。娃呀,那块火烧岩是风水宝地呢。人死了在里头也快活自在,祖先人看重生更看重死,归天的法儿也绝哟! 在书里,浩成读过巴人賨人悬棺青铜白虎的事儿,眼前的奇景却是实实在在的,他周身热血涌动,想到自己血管里恐怕也有部族英雄的血,顿时一把捏紧腰间那柄青铜短剑,喉头发痒真想对着那些石洞木棺大吼几声。瘸腿老人还在喋喋不休。往年子老子们要在岩下烧香烧纸,求祖先人保佑人和牛过滚牛坡平平安安,也有胆儿大的汉子搓起碗口粗的棕绳,从岩顶往下吊,想去洞里寻个宝贝。说来就神,人一进洞天变色风发吼,拴棕绳的树干叽叽嚓嚓叫唤,吓得人屁滚尿流往岩上爬。山有灵气哩,你不信我信,犯过岩洞的人不是病死就是摔岩。浩成捏青铜短剑的手起了汗。爹肯定是犯过岩洞的汉子,能从白骨堆里抓出这把剑该算是英雄了,可惜他终于没逃出瘸腿老汉相信的魔力,应了那本来不存在的魔咒,而化成一个使人闻之生畏的传说。他一直坚信,爹是被娘和那个被娘骂为骚狐狸精的女人一起爱死的,不然一个精明强悍熟悉山性的牛贩子不会跌下滚牛坡。春儿喜欢坐在岩岩上看牛贩子过路,却不怂恿他走这条牛贩子山道。浩成哥,今年秋季我们卖它几万斤粮食,揣一叠票儿去逛东乡城,再坐汽车逛绥定府,我们这山坡坡,只有当兵的黑娃毛狗茂林才贵看过那些花花世界,现在轮到我们看啦!你要买牛就去龙头岩,哥吔,千万要把细些稳当些,滚牛坡是阎王坡,莫学你爹要牛不要人。你这人,我要啦!她的脸红粉粉的,眼水雾雾的,再陡峭的滚牛坡也在浩成心里拉直展平,连爹的阴影也荡然无存。 破铃铛不响了,整个山谷突然沉寂,山道在一面险峻石壁前折断又从一片马桑黄荆葛藤芭茅混合的灌木丛中冒出来蛇一样往岩上爬。瘸腿老汉坐在路旁石上,吧嗒吧嗒抽烟,对石壁看也不看一眼,那紫黑色干皱皱的面颊却激动得抽筋般跳动。老人背后是一面缓坡,生得好特别,几百里大巴山都没见过这番奇景——蓝色的蓝天星红色的杜鹃花黄色的野金盏紫色的山葡萄白色的岩水仙绿色的菖莆叶血色的刺糖果;酱红的喇叭藤银白的蒲公英紫灰的马蹄莲橘黄的迎春花殷红的相思籽血紫的鸡冠草;白白的野百合黑黑的紫青藤黄黄的棋盘菊蓝蓝的毋忘我。星星点点团团簇簇,把一面坡涂抹得五彩缤纷。 俗话讲,好山才有好景,年轻人莫那样傻兮兮的看景致,它叫眼花坪,也带得有魔法,好些汉子就是被它迷下滚牛坡的哟。那些花花草草把祖祖辈辈人啊牛啊的血水汗水喝足了,才长得那么妖妖艳艳。走吧,放开牛,让它自家爬,牛也有副脑瓜子晓得把稳着实,记紧一句话——顾人莫顾牛。上坡吧,嘿什!——黄黄灰灰黄黄,莫把性命当儿戏哟。叮叮咣咣的破铃铛声把人心提起来往滚牛坡上挂。瘸腿老汉灵敏得像猴子在岩上跳。浩成心一横把牛们赶上了坡,他不信自己连个带残的老头都不如。咕哇!——咕哇!——早守候在岩缝间的鹞鹰飞起来,在山谷旋来绕去,展开的大翅膀把天也遮去一大块,使人头皮发紧肌肤发冷心子发毛。浩成的腿杆轻轻飘飘的,好像一阵小风都可把他卷起来,幸好有两条牛的重量把他压在岩壁上。瘸腿老汉眼睛有毒,他买的黄牯子脚有神力领着头一步一步往上爬毫不慌张,浩成的两条牛学着它的样儿挪动足蹄,不时还担忧地瞅瞅前面年轻的主人。 远望才叫惊心动魄。两个人三条牛像剪纸一样贴在偌大的空荡荡的石壁上,似乎鹞鹰的巨翅轻轻一扇就会把他们卷下深谷。叮叮咣咣的铃铛声,才使几个剪纸成为活物。浩成这时才悟出破铃铛的妙用,它有几秒钟不响心就发紧,响个不停心就松泛活络,干这勾当到底老牛贩子强。他不知爬了多久好像比往返一趟龙头岩还久,他把爹娘自己牛都忘了,唯独春儿在眼前晃动,笑盈盈情脉脉的……噗啦啦腿下的石头蹬翻一块,身子猛然下坠,若不是被系破铃铛的黄牯子用角顶一下他就悬空了,全身汗毛开闸样地淌冷汗,他趴在岩壁上像只四脚蛇。爹就是这样摔岩的!他大彻大悟了。爹对娘怀着愧疚,又痴迷于刚给过他野火般热情的女人,不撞鬼也要摔岩。 好险好险,年轻人啥也莫想,按住绳子牢牢抓死!瘸腿老汉不知啥时候已爬上岩端抱住一棵黄杨树,扔下来一根大指粗的棕绳子,他的心一下贴实了,不知怎么的泪珠儿像虫子痒痒地钻出了眼眶。嘿!娃吔娃吔,快上,牛着忙了要出祸事哦,娃吔。瘸腿老汉的脸平静得如一块山岩,浩成心头热热地攀着绳子往岩上蹬,他刚在岩头站稳,瘸腿老汉又山猴子一样顺棕绳滑下去,朝牛们哦哦地轻唱,护着它们走。牛们像羊儿一般温驯,小心翼翼跨过石骨子坡,上了岩头就扬颈高叫——哞啊!——哞啊!—— 十几里长的野猪峡回应着——哞啊——哞啊——
转载请注明:http://www.fdnmd.com/wacs/7137.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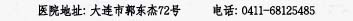
当前时间:
